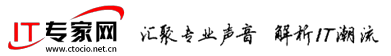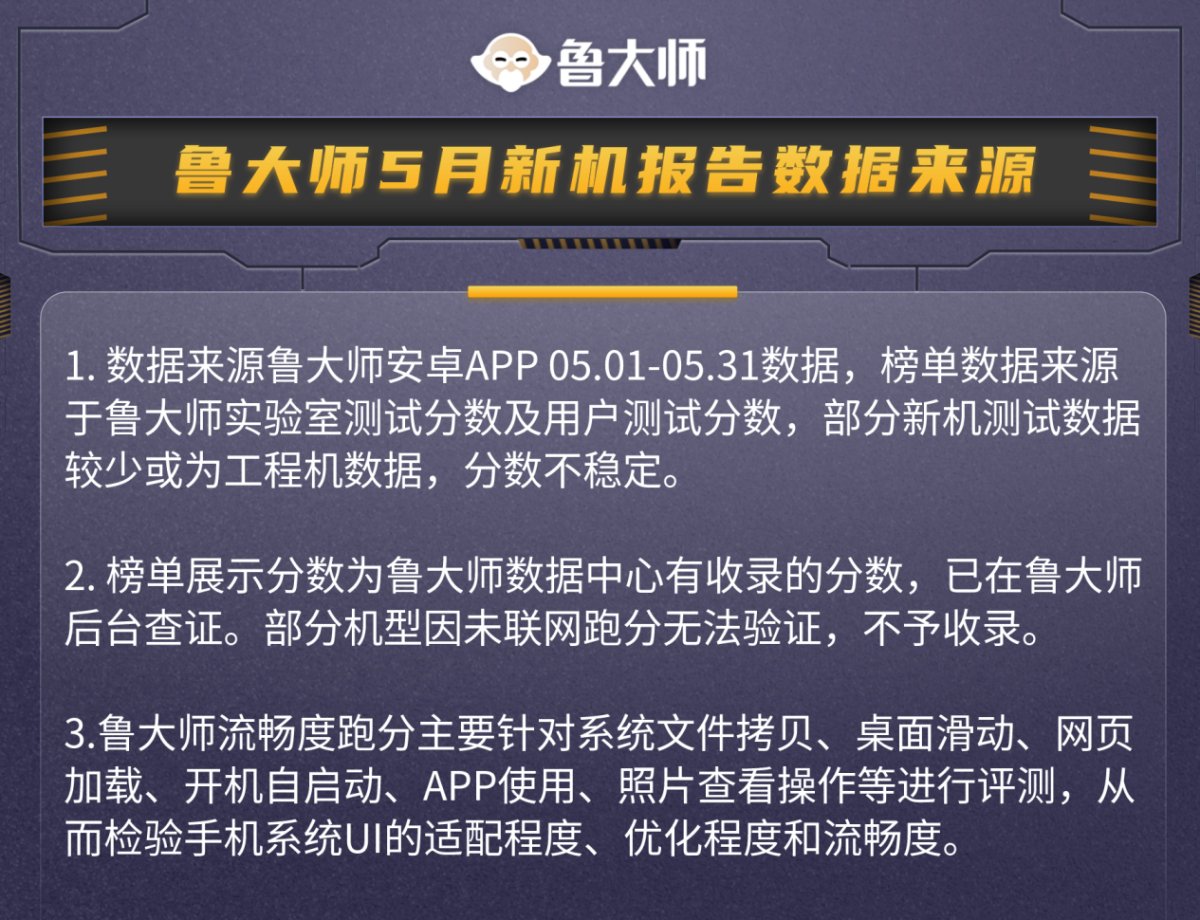作者:杨 勇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院 研究员
郑 悦 网舆勘策院特聘研究员
摘要
对游戏规则实行著作权的保护,名为提供著作权保护,而其实质却是借用著作权法的外壳对游戏规则提供了一种类似专利权的保护。以这一思路探讨游戏规则可版权性问题是不可取的。
与体育赛事录像保护的不同,其更多是保护体育赛事画面的表达,不可能涉及体育赛事的运动技巧和技术的著作权法范围保护。而游戏规则保护的主要是游戏的玩法思想。一旦将游戏规则的技术方案纳入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甚至将超越专利法保护模式,形成“玩法专利”和“玩法垄断”,对产业的发展或将带来负面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司法实践及学界一般基于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否认游戏规则具有可版权性。从美国80年代对早期经典游戏做出的判决到近十年间对新型手游、卡牌游戏所作的判决,无一不在对原被告游戏进行相似性比较的过程中将游戏规则排除了版权保护。我国司法实践一般而言也不认可以狭义著作权为游戏规则提供保护,而主张以竞争法对模仿其他游戏的行为加以规制。然而,近年来的司法裁判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2018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二审先后判决的“太极熊猫诉花千骨案”对传统观点做出了突破。该案中,法院指出,如果玩法规则是属于概括的、一般性的描述,则属于思想不构成表达;如果玩法规则具体到了一定程度,产生了足以使人感知作品特定来源的玩赏体验,就能够构成表达。近期,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率土之滨诉三国志”一案再次指出“电子游戏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学界亦有不少学者持有类似观点,其认为游戏规则中可能包含足够具体的、能够为著作权所保护的表达。上述观点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有力的“破局”,例如苏州市中院详细的游戏规则玩法比作电影情节,并提出游戏界面设计是游戏规则的特定呈现方式。广州互联网法院还论证反驳了功能性阻碍游戏规则获得版权保护的观点。这些观点之所以主张以狭义著作权对游戏规则提供保护,主要是由于其认为模仿他人游戏规则的“换皮游戏”大肆盛行,挤占了原创游戏开发商的市场,可能影响游戏市场的创新活力。那么,上述对传统上认为游戏规则不受版权保护的观点提出的“破局”或挑战性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上述观点并不正确,那么模仿抄袭他人游戏规则的“换皮游戏”是否有必要规制?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
二、对游戏规则的版权性保护实为以版权之名提供类专利法模式的保护
厘清游戏规则的概念是解读游戏规则是否有可能抽象概括出“表达”的前提。有学者将游戏规则的核心定义为供玩家共同遵守的一套制度,另有学者为此核心概念补充了一些游戏规则的特征,比如设置游戏初始状态、根据玩家输入作出反馈等。如果将游戏规则定义为“供玩家遵守的制度”,则意味着该种游戏规则必然能够直接以文字方式呈现,从而可供玩家阅读和遵照执行。这样的游戏规则一般存在于非电子游戏中。例如,传统儿童游戏“丢手帕”,其规则可表述为:玩家们围坐成一圈,由一名玩家手持手帕、边唱儿歌《丢手帕》边围绕着其他玩家慢跑;当歌声停止,慢跑的玩家将手帕随机丢在一名玩家的背后,发现背后有手帕的玩家应立即起身追赶丢手帕的玩家;若丢手帕的玩家先跑回所丢手帕的位置,则丢手帕者胜利,反之失败。这类可成文的游戏规则需要依赖玩家的阅读理解并主动执行,《三国杀》等卡牌游戏规则也属于此类。这类规则并不存在于电子游戏之中,因为电子游戏对游戏规则的执行依赖于预先编写好的计算机程序,由程序执行游戏规则、与玩家互动并作出反馈。比如,大型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玩家点击某一技能攻击特定单位,屏幕上显示红色数字“-3”,玩家即理解被攻击的单位损失三点生命值。可见,在电子游戏的玩赏过程中,玩家并不需要主动阅读和执行规则,而是通过对游戏的操作和系统的反馈来识别和了解规则。此时,游戏规则体现为对玩家在游戏操作过程中的行为设置限制,玩家只能在游戏软件允许的范围内实施行为,满足游戏软件预先设定的胜利条件即取得胜利。对于玩家而言,游戏规则分为可直接阅读的文字表达以及无法直接阅读、需要从与计算机软件的互动及其反馈中识别和理解的游戏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最终游戏规则以上述何种方式向玩家呈现,在游戏的设计开发过程中,为了便于开发制作工作的进行,游戏规则必然曾经以文字方式撰写于游戏策划案中。游戏策划案,即为游戏设计者撰写的一套指导构建游戏的操作方案。开发人员以此操作方案为蓝本,编写游戏软件的代码、设计和绘制游戏角色形象和场景、制作游戏动画,最终形成可投入运营的游戏产品。玩家能够从游戏互动中了解到的游戏规则是有限的。许多游戏为了趣味性可能对部分关卡、地图、角色或任务进行隐藏,由玩家自行探索和发掘。无论玩家如何进行游戏,都不会超出游戏开发者预先设计的玩法范围。这也决定了电子游戏中玩家所了解和掌握的规则和玩法必然少于等于游戏策划案所记载的游戏规则和玩法。非电子游戏也是同理,尽管游戏设计者无法通过程序对玩法加以隐藏,但玩家所发掘出的玩法依然不会超过游戏策划案记载的范围。若玩家另行设计出新的玩法,则该玩法也就不属于游戏开发者的智力成果。因此可以说,游戏策划案是对电子游戏的规则最完整的描述和表达。
由上述对游戏概念的解析可知,游戏规则早自游戏开发制作工作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而非游戏制作完成后才出现。而玩家所知的游戏规则只是游戏策划案所记载的完整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游戏策划案作为对特定游戏的规则和玩法最完整的文字记载,属于文字作品。在游戏(尤其是电子游戏)制作完成之前,对游戏规则的唯一呈现方式就是游戏策划案的文字表达。对游戏规则的特定表达固然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然而著作权法仅保护该特定表达,而不能阻止他人依照同一游戏策划案开发制作游戏。据此假设,游戏A的游戏策划案在游戏A未发行之前遭泄露,另一开发商根据游戏A的策划案开发制作了游戏B。两款游戏先后问世,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二者的规则和玩法是相同的,此时能否认定游戏B的开发商构成著作权侵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时,游戏B的开发商显然没有接触过游戏A,其软件代码、游戏角色、场景、动画等均为自行编写和制作,不可能构成对上述作品的抄袭。尽管游戏策划案所记载的是最为完整的游戏规则,但如果令游戏A开发商有权利阻止他人依照游戏策划案开发制作游戏,那么这一保护模式实质上保护的是策划案所记载的技术方案,也就是专利法模式,而与保护独创性表达无关了。如果允许游戏开发商以上述方式垄断特定游戏规则,则意味着允许其越过专利审查程序,还能获得远超出专利保护期的保护期限。可以认为,对游戏规则实行著作权的保护,名为提供著作权保护,而其实质却是借用著作权法的外壳对游戏规则提供了一种类似专利权的保护。以这一思路探讨游戏规则可版权性问题是不可取的。
三、游戏策划案的美感并未转移到游戏产品中
从另一角度出发,若游戏规则能否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那么游戏规则具有美感,不论这种美感是小众还是普世的,是高或低。并且,当特定作品被改编为另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原作与改编作品具有不同形式的美感,但原作中必然存在部分美感被转移到了改编作品中。例如,当漫画被改编为真人演绎的电影作品,虽然漫画原本作为美术作品的线条、色彩等美感难以转移到电影作品中,但其情节之美感则能够转移至电影这一新的表现形式之中。如果对原作品的“改编”没有将原作品的任何美感转移到新作品中,则根本无法认为新作品是对原作品的“改编”,说新作以原作为灵感可能更为合适。比如根据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所创作的同名电影,以画中少女为灵感,讲述了其作为女佣到画家家中工作、并成为画中被绘制的少女的故事。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并非原画作的表达,原画作的美感仅限于其构图、线条和色彩所形成的静态画面之中,而电影对原画作画面的再现仅有一个镜头。如果剪去这一个镜头,此时这两部作品只能说是在主题上互相关联,而不能认为新作品使用了原作品的具体表达。因为原作品的美感并未转移到新作品中。
另一种可能是,新作品在利用原作品时将原作品的美感进行了转化,从而使新作品呈现出的是不同于原作品的另一种美感。此时的新作品则由于构成对原作品的转换性使用而认定为合理使用。如在“Seltzer v. Green Day案”中,被告Staub在原告画作上添加了纵跨整张图片的红色十字以及局部的黑色条纹,将画作的寓意由“表现洛杉矶年轻人的时下文化”改为“讽刺宗教文化”。这一将原作美感全然改变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美感的行为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构成合理使用。
可见,无论是根本未转移原作的美感,还是改变原作品以形成截然不同的全新美感,只要原作品的美感没有转移到新作品中,新作品就不会因“未经许可使用原作品”而构成对原作品的著作权侵权。
如前文所述,游戏规则最初和最完整的呈现方式是作为文字作品的游戏策划案。游戏策划案的美感应当是来源于其语言流畅、逻辑严谨和用词精准,也就是语言文字之美。而当玩家操作游戏产品时,除非游戏策划案中的文字被转移到游戏画面中供玩家阅读,否则玩家已经无法感知到原策划案的文字之美。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感受到的美感分别来源于游戏中穿插的过场剧情的情节之美、画面、特效与角色形象等形成的画面之美等,这些美感原本并不存在于游戏策划案中,而是在随后的游戏制作过程中由开发人员添加的。除美感外,玩家所感受到的游戏体验中应当还包含竞技快感,而这种使玩家酣畅淋漓的体验就显然与著作权无关了。总结上述分析,若游戏规则存在美感,则其必然能体现于任何一种呈现方式中,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游戏规则最完整的描述——即游戏策划案中。而由上述分析可知,游戏策划案中所包含的美感仅为语言文字之美,其并没有丝毫转移到游戏产品中,那么玩家又如何能从操作游戏的过程中体验到所谓“游戏规则的美感”呢?由此可见,游戏规则本身并不具有著作权所保护的文学和艺术类作品的美感。
四、对游戏抽象概括后的可版权内容不包含游戏规则
判断游戏规则可版权性必要手段之一即进行抽象概括,进而辨别游戏规则是整体处于思想与表达分界线之上——作为思想,还是有部分落到了思想与表达分界线之下——构成表达。对此,司法实践和学者均提出了具有实用性的抽象概括法。
1、游戏规则不能类比为电影情节
首次认可游戏规则含有可受版权保护之表达的“花千骨案”主审法院提出了将游戏规则与电影情节相类比,从而认定了游戏规则作为一种“被充分描述的结构”,构成表达。广州互联网法院也在对“游戏规则可版权性”的铺垫论证中将游戏与电影进行比较,由此论证“游戏规则在游戏中具有了独立于游戏素材被感知和欣赏的地位”。事实上,将游戏与电影、小说等作品类比后进行相似性比较的做法早在2012年的“Spry Fox v.LOLApps案”中就出现过,而该案中,法院以同样的比较方法最终却排除了对游戏规则的版权保护。这表明,这两方持对立观点的主审法院在采用相同思路梳理思想与表达的过程中发生了分歧,从而使其中一方的结论有失偏颇。
事实上,在“Spry Fox v.LOLApps案”中,法院之所以提出将游戏与电影作类比,其目的是为了在游戏的相似性比较中适用混同原则和场景原则,而非将游戏规则与电影情节做同质性的比较。最终,法院通过追溯过往判例中曾出现的各类游戏玩法,剔除了奖励通关金币或分数、兑换游戏金币以获得游戏优势等玩法。
“Spry Fox v.LOLApps案”中,华盛顿西部地方法院提出游戏和电影剧本一样,也具有情节、对话、主题、氛围、节奏、角色等。其将游戏整体与电影整体进行类比,而并没有将游戏中的规则部分认为与电影中的情节相等同。而“花千骨案”则不然,苏州市中院认为“角色的选择、成长、战斗等玩法设置本身具有叙事性”,故这种详尽的、具有叙事性的玩法规则类似于电影情节。在游戏中,游戏角色的成长、战力的提升、战斗的进行等体现了事物的发展,这一点与情节的发展具有相似性,但能够体现事物的发展不意味着能够受著作权法保护。比如电影作品的故事梗概作为电影情节的进一步抽象,也是能体现事物发展、具有叙事性的,而由于电影的故事梗概抽象程度过高,其仍然落到了思想范畴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可见,电影情节能够享有著作权的根本原因是其足够具体,是对电影思想的确定性的阐述,而非叙事性。因此,仅以叙事性这一特征不足以推断游戏规则相当于电影情节,也不能推断游戏规则与电影情节落在思想与表达金字塔的同一位置。
2、抽象思想仍可以被“独立感知”
就“率土之滨”案中游戏规则是否能被“独立感知”的问题而言,抽象的思想并非不能被独立感知,能被独立感知的未必落入表达。就文学作品而言,无论抽象程度多高的思想都依然可以被读者所感知,而就相同的思想所创作的不同表达仍使这些文学作品构成不同的作品,而非对彼此的复制或改编。《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向读者传递出青年人困于家族枷锁、无法追寻自由爱情酿就的悲怆感,而即便思想内核完全一致,具体情节的填充使二者成为东方与西方对仗而不相同的两部独立史诗级文学作品。电影《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五月八月》均讲述了完全相同的历史事件,亦都表达了对侵略者恶行的痛斥和苦难中的人民对生的渴望,而影视作品创作的空间无际无涯,对完全相同的事件仍可以形成多样化的表达。抽象思想当然能被“感知”,且其感知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表达相对独立,具体情节的改变不太能影响故事的核心精神,至多使得故事的可看性和精彩程度有所变化。因此,广州互联网法院关于“独立感知”的论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独立感知”与否,不影响对思想还是表达的判断。
3、足够具体的规则仍是规则
“花千骨案”中提出了另一重要“破局”观点,即足够详尽、具体的规则可以构成表达,这一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需要明确,在著作权法中,并非只要足够具体就足以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还应当满足一些消极要件。尽管我国《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消极要件目前仅包括官方正式文件、时事新闻、历法、通用数表等情形,但我国所参加的一些国际公约早已详尽列出不受版权保护的情形。比如《伯尔尼公约指南(1971年巴黎文本)》第2.3条指出,思想不受版权保护是公约的一项基本要求。TRIPs协定第9条第2款也说明了版权保护应及于表达,而不及于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数学概念等。WCT第2条对于版权之保护边界的规定重复了TRIPs协定第9条第2款的规定。思想、程序、操作方法等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对象,许多国家也选择在其立法中明文加以列举。如《美国版权法》第102条(b)款将以任何形式描述、解释、阐述或囊括的思想、程序、过程、系统、操作方法、观念、规则或发现等均排除至版权保护之外。《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259条第5款规定著作权法不适用于思想、概念、原则、方法、过程、系统、解决技术、发现、事实等对象。《巴西著作权法》第8条不仅在第1项将思想、标准程序、系统、方法、设计、数学概念排除版权保护,甚至在紧接着的第2项明确将进行智力活动、游戏或商业活动的方案、计划和规则排除保护。尽管各国立法的具体用词各不相同,但仍与TRIPs协定的规定达成了高度一致。
不论如何描述游戏规则,其本质上仍属于指导玩家进行游戏的操作方法或是限制玩家操作范围的系统,与国际公约及各国立法所规定的程序(procedures)、操作方法(methodsofoperation)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并非只要足够具体,规则就能成为受保护的表达。即便规则异常详尽、具体,其仍然只能是“具体的规则”,而为版权保护所排斥。
4、对游戏的抽象概括使规则最终被排除
在抽象概括的过程中,若正确区分游戏规则与游戏规则的表达,最终能够将游戏的规则予以剔除。例如“DaVinci Editrice S.R.L. v. ZiKo Games案”中,德州南部地方法院将规则、步骤、获胜条件等与游戏中的表达性元素(expressive elements)做了严格区分,并指出规则等因素仅仅是帮助构建了表达性元素,但其本身不受保护。
反之,如果将游戏规则的表达误认为是“足够详尽的游戏规则”,则有可能得出详细的游戏规则可以受版权保护的结论。有学者按照游戏规则的具体程度由低到高,将游戏规则区分为基础规则、一般规则、具体规则,并指出具体规则能够构成表达。而在阐述具体规则时,却指明具体规则是“直接以文字、声音或图像等方式告知玩家的游戏规则。”根据其对“具体规则”的表述,可知所谓具体规则其实就是指以文字方式向玩家呈现、或以声音朗读的游戏规则说明书。实践中已经有案例认定游戏规则说明书能够作为文字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故上述对不同游戏规则抽象、具体程度的区分并不能证明游戏规则具有可版权性。同样的,“花千骨案”中法院的论述也明显体现出其将游戏规则的表达误认为是详尽的游戏规则,其提出的“将单个游戏系统的具体玩法规则或通过界面内直白的文字形式或通过连续游戏操作界面对外叙述表达”以及“通过绘制、设计游戏界面落实游戏规则的表达”其实就是游戏中的文字及画面。由此可见,本案所意图保护的仍然是对游戏规则的表达,即文字和画面,其实并非是游戏规则本身。
综上,不论是与其他作品类型进行类比,还是对游戏作层层抽象概括,最终所剩余的应当受著作权保护的表达均不会包含游戏规则。
五、余论——“保护游戏规则”无须执着于著作权法
尽管近年来的许多观点都提出需对游戏规则以著作权加以保护,从而规制“换皮游戏”现象。但其所主张的保护模式并非版权保护模式,而是企图将游戏规则作为技术方案控制他人实施的专利法保护模式。同时,游戏策划案作为游戏规则最完整的呈现方式,其美感并未转移到游戏产品中,更遑论为玩家所感知。通过在具体的案件中对游戏规则进行抽象概括,能够提炼出可受版权保护的对游戏规则的表达以及不受版权保护的游戏规则本身。
与体育赛事录像保护的不同,其更多是保护体育赛事画面的表达,不可能涉及体育赛事的运动技巧和技术的著作权法范围保护。而游戏规则保护的主要是游戏的玩法思想。一旦将游戏规则的技术方案纳入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甚至将超越专利法保护模式,形成“玩法专利”和“玩法垄断”,对产业的发展或将带来负面影响。
在厘清上述观点后,即可明确,若某一游戏仅利用其他游戏的规则,而未使用文字、画面等表达,则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无需以著作权规制。换皮游戏行为,其本质上属于商业模式的复制,于市场自由竞争无碍。当换皮游戏因复制他人设计的游戏规则而获利,若新游戏在画面、故事情节、技术进步性等方面超越旧游戏,则旧游戏遭淘汰,玩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当换皮游戏的画面、故事情节、技术进步性等其他因素不如旧游戏,则新游戏无法取代旧游戏的市场地位,将很快遭到淘汰。市场中的不同主体必然会在同一商业模式下展开资本、技术、情节设计等各方面的竞争,无论如何,玩家将成为最终受益者。
如果确实有某一游戏公司开发出一款玩法独树一帜的新游戏,并且消费者已经将这款游戏与该游戏公司建立起稳定的对应性认知,若是有其他游戏厂商以混淆、误导的手段引导消费者去玩“换皮”后的游戏,则此时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这样的行为予以法律规制。
我国著作权法来源于国际公约,其保护范围和力度不宜突破国际公约。毕竟与世界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发展相比,我们更多是追随者。从国际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立法精神来看,既要保护著作权,也要保护传播,同时兼顾公众利益。既要保护创新,也要保护竞争,同时兼顾公平。过度的保护,有利于权利人的垄断利益,但未必有利于产业的良性竞争,未必有利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本文转载自网舆看策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