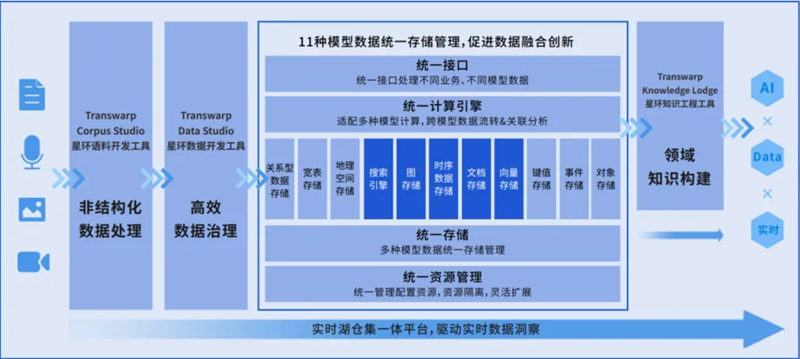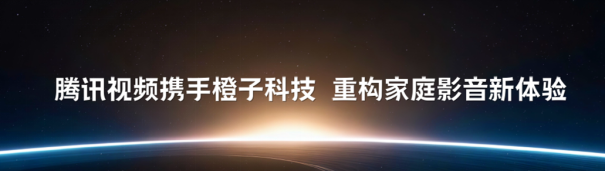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产业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正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在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的第八届物流包装技术发展大会上,箱箱共用创始人兼CEO廖清新发表了题为《中国循环包装产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跃迁的机遇与路径》的主旨演讲。作为连续第四年受邀参与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他首次系统提出了“三好模型”:每投入1亿元循环包装资产,预计可在未来十年累计撬动约5亿元GDP增量、创造400个就业岗位,并实现8万吨碳减排。此外,他还从“资本力、产品力、服务力、数字力”四个维度深入阐释了企业如何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从“制造思维”迈向“服务思维”、从“短期主义”走向“长期主义”,为行业服务化转型勾勒出清晰的实践路径。

本届大会以“数循共生 包链新态”为主题,汇聚了政府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及200余家企业的300余名代表,围绕物流包装的绿色化、智能化与循环化展开深入研讨,共同展望数字化时代的产业新图景。
循环包装进化:从产品到服务的“三好”模型过去几年,循环包装行业迅速发展,但更多聚焦在“绿色”这一概念本身。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视角,是其背后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机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GDP中的占比约为30%,而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已达50%。随着制造业不断向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迈进,对配套服务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果生产性服务业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将释放出近三万亿元的增长空间。其中,如果物流包装占1%,每年也将带来数百亿元的新增市场,潜力巨大。循环包装企业该如何准备,迎接这轮结构性机遇?
回顾十多年的行业发展历程,廖清新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这一过程:从最初的“周转箱”,到后来的“循环包装”,再到如今更强调服务属性的“包装循环”。当循环包装从一个产品进化为一项服务时,背后隐藏的“三好模型”也随之显现:
其一是显著的1:5GDP增长效益:1 亿元投入到循环包装,第一年带来 1 亿元制造收入;随后十年,每年再带来 1 亿元服务收入,十年累计就是10亿元,形成1:11长期收入带动效益,按行业增加值率折算,预计合计带动 GDP 增量约 5 亿元。其二是突出的1:400就业带动效益:以1亿元投资带来的制造产值为例,按照人均50万元年产值计算,可直接创造200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此外,在未来十年中,每年1亿元的服务型收入将带动200个服务业岗位,形成1:400的就业带动效应。其三是直接的1:80000吨减碳效益:以可折叠液体 IBC 为例,1 亿元循环包装投资意味着未来十年带来400万箱次循环。按此前 BSI 核算数据,每箱次相比一次性包装减碳 202 kg,十年累计碳减排达8万吨。
产业升级路径:从表象到实质的“四力”引擎现场廖清新进一步分享了他对产业升级路径的深入思考,详细阐述了如何以资本力、产品力、服务力与数字力“四力协同”作为关键引擎,推动企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跃升的战略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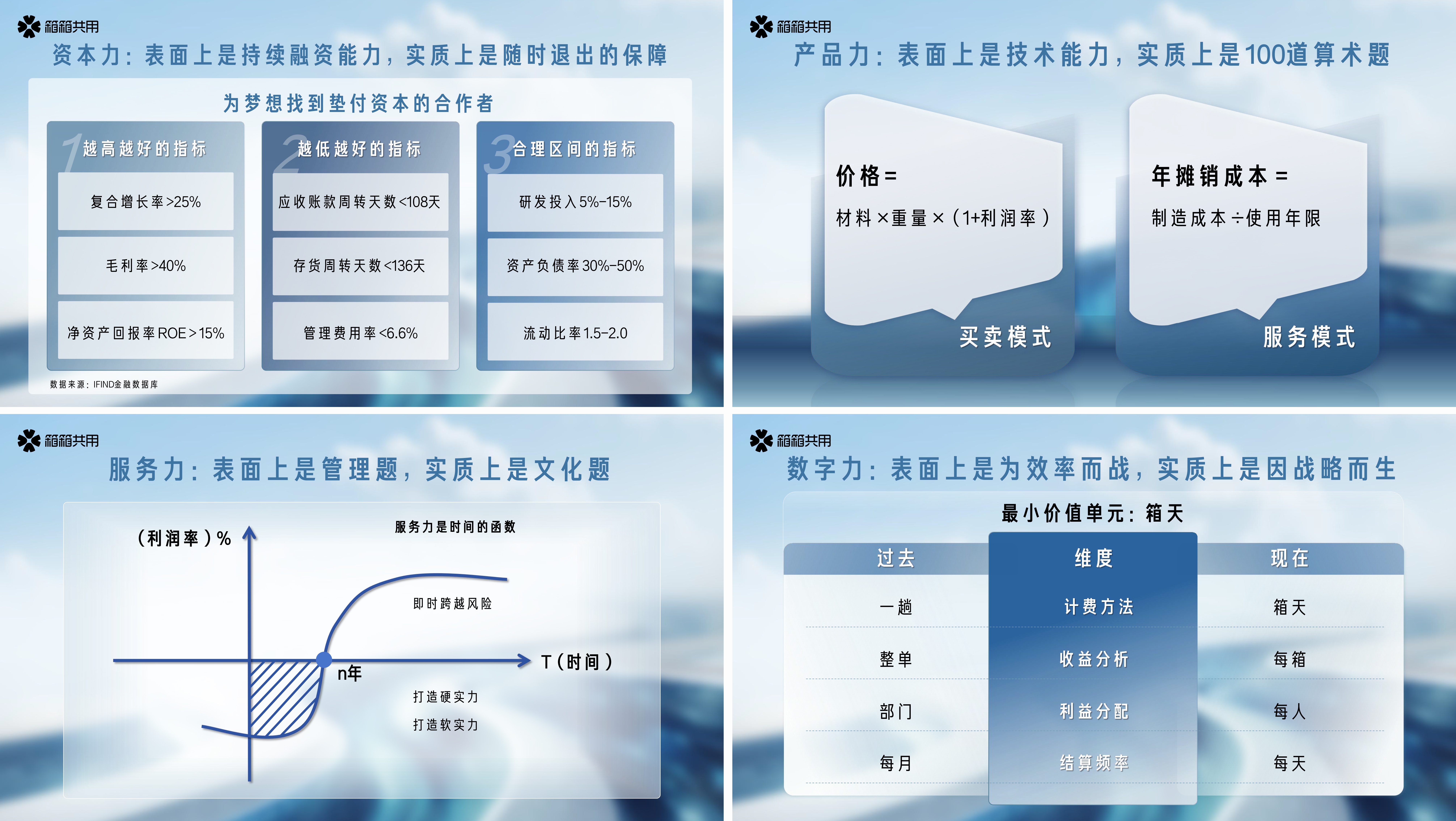
一、资本力:表面上是持续融资能力,实质上是构筑随时退出的保障
在企业的创立与发展进程中,创始人最为关键的任务之一便是寻找那些愿意为创业梦想“垫付”资本的合作伙伴,之所以称为“垫付”,是因为未来必须以超额的回报来偿还,垫付不是支付。因此,创始人必须时时刻刻关注企业的经营数据,并以此构建一个让投资人有随时退出的价值保障体系, 就像人的健康指标一样:刚出生的孩子各项指标可能都很健康,但企业恰恰相反,初期指标往往较差,随着战略推进和科学经营,这些指标会逐步改善。其中,有一些指标是越高越好的,比如复合增长率、毛利率、净资产回报率(ROE);还有一些则是越低越好的,如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存货周转天数、管理费率等;还有一些处在合理区间的结构性指标,例如研发投入占比和资产负债率等。他指出,企业最基本的任务是用净资产创造净现金流,通过周而复始地强化从资本到资产、从资产到收入、从收入到利润、从利润到现金、从现金再到资本的闭环效率,从而为垫付者带来超额价值回报的能力。
所以,资本力表面上看这是持续融资的能力,但实质上是凭借完善的价值增值体系为资本垫付者打造随时可以退出的保障能力。
二、产品力 ,表面上是技术能力,实质上是100道算术题
他指出,过去企业主要在产品销售领域展开竞争,普遍采用“成本定价法”,即用料工费成本乘以重量再加利润。因此,企业为了竞争只能在材料、重量或利润率上压缩空间,长此以往,传统的卖产品模式往往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薄,品质越来越差。但如果进入卖服务模式,企业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延长产品的寿命。因为寿命越长,每年的摊销成本就越低。这就要求企业把产品做到极致,用更好的材料、模具、工艺、设备,延长使用寿命,从而降低年度摊销成本,提升利润空间。因此公式的转变带来整个产业发生本质的变化——从短期思维转变为长期主义。
要把产品力做好,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如何把产品做到极致;二是深刻理解用户与行业的需求和痛点。用户的痛点往往体现在日常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例如在未来十年时间里,如何实现总成本最低——包括清洗成本最低、人工搬运成本最低、维修成本最低、物流成本最低。这实际上是一道面向用户的“算术题”。而前面所讲的是面向产业的“算术题”。只有把这两类问题结合起来,找到上百个关键问题的最优解,企业才能真正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构建起真正有黏性的、可持续的服务能力。
所以,产品力表面上看是技术能力,实质上是100道算术题。
三、服务力,表面上是管理题,实质上是文化题在从产品走向服务的战略转型过程中,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服务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长期的时间沉淀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进入新业务领域、搭建运营网络的初期阶段,企业往往需经历长达一年至三年不等的亏损期。在亏损期内,企业需要以投资视角看待亏损,并以“客户永远是对的”为基本原则,同步打造服务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以箱箱共用为例,在为某新行业客户提供循环服务的初期,需要构建覆盖公路、铁路、水路的收发箱网络,以及其他全套的硬实力投入,这包括包装资产池、人员、场地、自动化清洗设备、数字化系统等等。而在软实力建设方面,企业需要升级供应链,将故障率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并承诺在客户以及客户分布在全国的下游客户遇到任何问题时,能够提供7×24小时的服务和支持,确保及时响应。服务的本质是赋予客户“即时跨越风险”的惊喜体验。作为提供服务的企业要从亏损期中踩过的“坑”和经历的风险中总结经验,建立一套安全可靠的运行体系,让客户从第一天起就能获得稳定、可预期的服务体验。因此,从决定提供服务的那一刻起,企业就应树立“客户是用来宠的”的理念。
所以服务力,表面上是管理题,实质上是文化题,更依赖于企业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良心来滋养。四、数字力,表面上是为效率而战,实质上是因战略而生
一种常见的误区是认为数字力就是不断投入IT技术、IOT软硬件技术,甚至盲目跟风去投AI,将数字力单纯理解为技术范畴的概念。另一种误区是认为数字力就是仅限于建设企业的业务管理系统,实现异地办公、并发和协同,认为只要有数字化的系统,效率就有依靠,企业发展就有希望。实际上,企业构建数字力的核心在于定义最小颗粒度,重构最小价值单元,并基于最小价值单元,形成收钱、算钱和分钱和结算的操作系统,最终推动创新业务的复制和裂变。
我们身边有许多从产品走向服务的真实场景,从中可以体会到这些场景内核进化的逻辑。比如说从卖咖啡豆到卖咖啡,过去是以斤为单位卖,现在是以杯为单位,这种对最小价值单元、最小颗粒度的重新发现和定义,不仅改变了企业的性质,还调整了企业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以及扩张的路径。
对于循环包装也是如此。过去向用户收费是按照一趟多少钱,而现在是基于“箱天”(每箱每天)作为最小单位,根据用户占用箱体的数量和天数计费,并以此计算成本、毛利和业务激励。因此,发现更细颗粒度的最小价值单元,是业务进化的基础。基于“箱天”这个全新的最小价值单元,将过去的“按趟收费”转变为“按箱天收费”;从项目整体的订单收益分析,变为每个箱子、每个ID号的收益分析;从每个部门到每个人;从每月到每天、每单。
所以,数字力是一种创新业务的能力,表面上看是解决效率问题,而事实上是战略的颠覆式升级。在演讲结尾,廖清新以《西游记》为引喻,阐述了“从制造走向服务”的实战心法:“每个时代都有等待我们去取的真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我们修成正果的机会。孙悟空神通广大,一个筋斗云就可以将唐僧送达西天。然而,唐僧自始至终双脚着地,一步一个脚印,亲身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取不到真经。因此,作为创始人不能有侥幸心理走捷径,一定要躬身入局。关键时刻,一号位必须先上刀山、下火海。要明白‘钱买不到真经’,仅仅依靠‘定战略、搭班子’就想取得真经也是一种幼稚病。现实的成长路径是先凭借肉身与磨难搏斗取到真经,再携真经带领企业修成正果。”